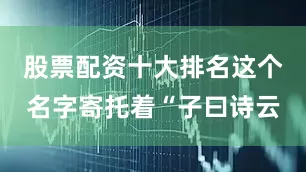
“1997年8月16日早晨,你看这条消息了吗?”洛杉矶唐人街茶楼里,70岁的刘老捏着《世界日报》,抖了抖报角。
那一天,《世界日报》刊出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:陈独秀的小女儿在美国被儿子弃养,濒临流落街头。对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来说,这不啻晴天霹雳——辛亥元老兼“五四旗手”的后人,竟落到如此光景。消息顺着传真和电台,一路传回香港、上海、安庆,人们这才把记忆翻到一个被尘封的角落。

时间往回拨到1912年。那年腊月,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回到故乡安庆。年关将至,年仅20岁的高君曼在青砖老屋里生下一个女婴——陈子美。这个名字寄托着“子曰诗云,美好传家”的朴素心愿。可惜,短暂的宁静很快被父亲的政治风暴打散。
1915年前后,陈独秀在上海办《青年》杂志,抨击旧礼教,忙得三天两头不归家,却总会抽空把女儿抱到膝头,用安庆口音逗一句:“阿囡,想吃桂花糖吗?”这是小女孩童年里屈指可数的温情片段。

命运第一次拐弯出现在1925年。父母感情失合,高君曼带着子美、鹤年迁至南京。三年后,高君曼病逝,家中顿时失去经济支柱。17岁的子美被迫辍学,在杭州电信局当电话接线员,从此养成坚韧不服输的脾气。那时她或许没想到,这份“凡事要靠自己”的信条,将陪伴她七十年。
杭州的工作枯燥却稳定。张国祥的出现,让单调的日子起了波澜。张祖籍宁波,做绸缎生意,谈吐温吞,人却勤快。老人家念及子美出身书香,劝她嫁个商人好避风头。子美点头,婚事便草草成了。短短数年,她连生三子。表面是“小布尔乔亚的宁静”,背后却暗流涌动。
有意思的是,婚姻裂缝并非源自金钱,而是张国祥的“表妹”。邻居一句“那可不是表妹,人家说是原配”,让25岁的子美五雷轰顶。夫妻争执后,张国祥答应与原配脱籍,却从此放纵花天酒地。抗战爆发,生意全盘停顿,两人领着孩子流落重庆、贵阳、香港,再回上海。一路逃难,子美白天跑码头倒腾布料,晚上埋头看《产科学》。她明白,只有掌握一门手艺,才有活路。

上海解放后,地摊生意难以为继。子美考了市卫生局的“接产员”证,在里弄帮产妇接生。那是一份苦差,三更半夜家属敲门,必须立马提着药箱赶去。舍不得搭车,她常步行几公里上门。邻里说她“心狠”,因为接生时手起剪落,干净利索;也说她“心软”,出诊若见穷人,总自掏车票钱。
可惜,第二段婚姻同样不顺。推土机司机李焕照比她年轻十岁,自负力气值钱,看不惯前夫所生孩子时不时来探望。鸡毛蒜皮磨碎感情。到1966年前后,大字报把她“倒卖布匹”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罗列成册,还加上一句“陈独秀反党余孽”。她被揪到街上批斗,剃阴阳头,抄家后连风湿膏也没留下。

就在这时,子美动了“走”的念头。1970年9月一个闷热夜晚,她把五只装菜油的铁桶两两捆成浮筒,带着与李焕照所生的两个儿子从深圳盐田下水,漂了将近十小时,拖着满身海腻登上香港大屿山。同船的年轻人都被警察遣返,她因为年近花甲获准临时居留。有人叹“老太太命大”,她嗤笑:“命大?命苦才对。”
在九龙城,她和儿子进纱厂摸浆纱线,三班倒,手指磨出血泡也咬牙坚持。攒下第一笔钱时,她没买金饰,而是租了四十平方米的房子,开了家“托儿所”,顶着《产科护理证》接零工。港府传出“清剿偷渡客”,子美立刻办旅游签,飞洛杉矶探亲。此后以技术移民身份留下,又花数年把两个儿子弄到美国。她本以为苦尽甘来,却不知真正的荒凉在后面。
进入八十年代,两个儿子各自成家,先是搬出公寓,接着电话也少了。1982年,子美突发脑梗,住院十天,回到公寓发现积蓄被窃,只剩一本《黄帝内经》和几件旧衣。每月570美元政府补助,扣掉400美元管理费就见底。她去找儿子,门铃响了半小时没人应。回到街角巴士站,她冷笑一句:“我当年把你们捆在铁桶上,如今连桶也值不起一顿快餐。”

也是那年,《世界日报》记者收到一封手写信——“我是陈独秀之女,现年七十,濒临老无所养……”,字迹歪斜,却干净有力。华人慈善会介入,替她还清欠费,供给伙食。这才有了1997年的那篇报道。
子美想回大陆。她向旧同事写信:“儿时的安庆河滩还在吗?我想看一看母亲的坟。”然而护照过期、身体欠佳、手续繁琐,计划一次次搁浅。2004年3月,她因呼吸衰竭住进加州长老会医院。护士在床头柜发现一本发黄相册:陈独秀抱着幼女,黑白合影已起卷边。

92岁那天凌晨,子美停止呼吸。无人守夜,院方依程序联系殡仪馆。三日后,旧金山《星岛日报》刊登讣告,篇幅不足两百字。有人感慨:命运开了个残酷玩笑,让一个曾被父亲捧在掌心的小姑娘,在太平洋彼岸孤身谢幕。
试想一下,如果当年批斗未起,若偷渡途中沉海,若美国的儿子良心未泯——任何一个环节稍有不同,都可能改写结局。可历史没有假设。陈子美的一生,如漂泊海面的一盏孤灯,微弱却倔强。她的故事提醒后人:政治风浪固然惊心,亲情的冷暖同样足以颠覆一个人的世界。
盛达优配-盛达优配官网-正规实盘配资股票-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